新冠疫情重压下的感染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杜玮 彭丹妮 杨程晨
医院感染科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然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龚作炯却指出,实际上,武汉市当地多家市属医院都长期没有开设感染科。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很多患者都被集中在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令该医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受了无法承受的压力。
2003年SARS结束后,中国曾迎来一轮感染科的发展热潮。然而,17年之后,在眼下这场新冠病毒阻击战中,原本应是主力军的医院感染科,却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人员、场地、设备均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兼肝病中心主任王贵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国家需再次重视感染科的发展,感染学科的发展应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建设的路径上来。
因病而变的感染科
王贵强的办公室位于北大第一医院门诊楼南侧一栋灰色老旧的三层行政楼内,行政楼一层从今年1月23日起开设发热门诊,他所在的感染科全员上阵。开设之初,每天有上百门诊量,最近的门诊量为每天二三十。北大第一医院也是国内较早设立感染科的医疗机构之一,只不过那时的感染科还叫传染科。
1950年代,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等经典传染病还在中国流行。为更好防控这些传染病,1955年,当时的国家卫生部出台了《传染病管理办法》,随后各大学附属医院纷纷成立传染科。北大第一医院传染科即于1955年成立,创始人是时任医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吴朝仁。“当时传染科的力量非常强大,国家重视,传染科由精英人物组建。”王贵强说。
这种专门治疗传染病的学科模式,被称为苏联模式,这也是国内绝大多数医院最初建立传染科采用的方式。传染科设有隔离病房,与此同时,当时国内多地还建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北京最早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为地坛医院,1946年建成。
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模式。当时,像中国国内流行的经典传染病在美国等已较为少见,医生接诊以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为主,比如说,神经系统感染、败血症、尿路感染等,这样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感染科。
中国感染科的发展路径,复制了西方曾经走过的路。哈佛大学医学文化学教授大卫·琼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0年代以前,欧美几乎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是传染病学专家,因为对付传染病是他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当时,医生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各种感染性疾病,轻如感冒、腹泻,严重如天花、肺炎、小儿麻痹症??20世纪初期,传染病是人类疾病的前沿与中心。
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已经弥漫着一种自信:征服各种传染病已经指日可待。几乎每一周,医疗机构都会宣布,在人类同传染病的战争中又取得了“奇迹般的突破”。1940年代初抗生素的发现,到1965年25000多种抗生素类药物的研发、1955年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等事件,是这种自信的来源。1967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宣布,对感染性疾病的战斗已经赢得胜利。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不需要再独立设置传染性疾病科。但随后,艾滋病的出现,给了这个领域当头棒喝。
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到了1980年代,中国人传染病的疾病谱也发生变化,霍乱、血吸虫病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病毒性肝炎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感染性疾病。1970 年代,由于农村卫生条件落后加之人口出生率高,乙肝在中国迅速暴发。尽管随着乙肝疫苗于1975年的成功研发,中国的乙肝发病率有了显著下降,但截至2019年,全国仍有8600万乙肝病毒感染者,肝炎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医院感染科的主要“客户”,长期就是各类肝病病人。
在“肝病大国”的帽子迟迟不能甩掉的同时,艾滋病、肾综合征出血热等新发传染病也陆续出现。自1985年中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中国的艾滋病患病人数曾在此后10年里增长缓慢。但从1995年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快速增长期,截至2018年9月,全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患者共85万人。
1984年,王贵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阜新市传染病医院工作。起初,他还能接触到流脑、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后来,慢性乙型肝炎病例逐步增加。1980年代,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成立,病毒性肝炎就是其主要防治内容。“病毒性肝炎的治疗相对比较简单,以肝脏受累为主,除了大出血需要抢救,其他没太大难度”。
1990年代后,随着疫苗等防控手段的出现,经典传染病的发病率进一步下降,病人减少,传染病的病种也越来越少。今年82岁的翁心华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也是国内感染学科的泰斗人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传染病患者数量的减少,医生们另谋他业,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传染科的规模出现萎缩。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友明在这一科室做医生已有31年。他刚进入传染科时,科室还有40张床位,此后,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传染科逐渐减少,到2003年SARS前后,传染科只剩下15张床位。但他对此表示理解,“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缪晓辉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1998年,他接手长征医院感染科时,这是一个“无论文、无基金、无成果”的三无科室。2000年,医院要大力发展骨科,院领导想将拥有三十多张床位的感染科病房转作骨科病房,撤掉感染科,科室人员一部分去肾病科,另一部分人分流到长海医院,缪晓辉去做消化内科主任。缪晓辉不同意,找院领导据理力争,感染科才得以保留,但科室却被迫搬到医院三公里之外的一个由毛纺厂改建的康复科里。
面临生存危机的不止综合医院的感染科。2003年SARS前,因传染病患者大幅度减少,地坛医院曾一度面临被撤并入北京另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佑安医院的命运。当时,北京市卫生局表示,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规模也就两三百人,两家医院都吃不饱,浪费资源。但在SARS时期,地坛医院收治了329名病人,危重症病人占到50%以上,对阻击疫情起了巨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地坛医院的命。
而传染病的大幅减少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学科发展方向的改变。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北大第一医院的斯崇文教授彼时任主任委员。在三年前,北大第一医院已经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疾病科。到2002年,上海华山医院传染病科教授翁心华担任第七届分会主任委员时,分会正式更名,全国各级医院也相继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科。
17年里的倒退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陈永平至今还对2003年抗击SARS时记忆深刻,设备仓库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用砖墙垒起来做物理隔离,一间病房里住四五个人,病区只开出一个小门给医生进出,没有“三区两通道”,根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SARS过后,陈永平与院领导都觉得要加强感染科建设。2012年,医院感染科搬进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大楼,整栋楼负压设计,提供160多张床位,有移动CT等设备,医生和患者分别从地下一层和地上一层进入病区。新冠疫情中,作为浙江省级的定点医院,温医大第一附院共收治了近百名疑似及确诊患者。
翁心华记得,当年SARS发生后,原卫生部官员到上海了解三级医院感染病科发展情况。“我和他讲,医院里最破烂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病科”,这名官员回去后,就给上海市的医院拨款,加强感染科的建设。2004年,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须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但能有陈永平科室这样发展的仅为极少数。2003年,赵晖所在的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新建了隔离病房,当时在浙江省内也属先进。但17年过去,医院其他科室病房不断更新,赵晖所在的感染科还是老样子,当甲流H1N1、手足口病等疫情来袭时,病房根本就不够用。陈永平曾多次到温州及周边市县医院考察,他发现SARS过后的17年间,很多医院的感染科“基本没有发展”,应对此次疫情,有的医院依旧是医生和患者走同一通道,有的医院连隔离病房都没有。
杨友明工作的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虽然有70张床位,但病房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不符合隔离条件。SARS过后,医院曾建了20张床位的标准隔离病房,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面对激增的病人,医院只能再将外科系统的病房整体改造,腾出400个床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谢青等曾针对上海市57家二甲及以上综合医院感染病学科现状做过调查。2019年9月,他们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综合性医院感染科设置率为100%,但二级医院感染科病房设置率只有20%,总床位数328张,三级医院病房设置率要高一些,但也仅刚过一半,达55.56%,总床位数799张。
武汉市一家二级综合医院——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该院感染科只有3个人,算是医院规模比较小的科室,当地其他二级医院感染科的人数也都与红会医院差不多,红会医院感染科一般不会收治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病人,而是选择将其转往金银潭或肺科医院住院救治。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陈国强等在其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武汉市的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武汉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1400万, 而两所专门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和肺科医院床位共900余张, 0.64床/万人, 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与此同时,武汉市综合性医院内传染科体量非常有限。
1990年代以来,医疗开始市场化,感染科成为不赚钱的科室。王贵强分析说,虽然SARS以后,传染科改为了感染科,但不少医院的感染科依然以看肝病、结核为主,传染病发病率下降,带来了科室业务量的减少,进而效益下降。而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的接诊都有季节性,发热病人多在冬春季节,肠道疾病集中在夏秋发病,而且两个门诊看病人数都不多。以他所在的北大第一人民医院为例,大约4年前,一年的肠道门诊、发热门诊总量分别为1万例出头,平均下来每天只有三四十例病人。浙江乐清市人民医院的年门诊量为7万多例,这在同等级的县级医院已属于前列,其中,肝病占50%,结核占15%,不明原因发热占20%,还包括艾滋病等其他疾病。杨友明说,湖北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感染科1年总的门诊量才1万例左右,发热门诊多的时候每天十几个病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个,工作量远远不饱和。
赵晖将感染科的工作形容为“赔本买卖”,一方面,感染科的病房设置需要单独且较大的空间,病人因为要满足隔离条件,有些不同病种的病人不能安置在一起,使得床位的利用率不能达到100%;另一方面,感染内科以药物治疗为主,不像外科那样使用各种器械,随着药品零加价政策的实施,加之结核、艾滋病的药物都是免费提供,令感染科的收益变得极为有限。
“打个比方,肠道门诊一天一个医生可能只看10个病人,产生的利润还不够医院给你发工资的。我出一天肝病门诊,大概有120~150个病人,开一些检查单、化验单稍微还能赚一点,很少有其他产生利润的地方。”赵晖说,医生查个房只有三五块钱。而相比其他科室,感染科必须要用的医用防护用品又是一部分不小的支出,这使得医院没有发展感染科的动力。杨友明则表示,来感染科看病的人大多经济条件不好,穷人比较多,有些慢性病比如说肝炎等需要较大的支出,这还导致一些人因病返贫。由于担心无法承受治疗费用,有些人甚至选择不来看病。
收益不好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科,以看肝炎、结核为主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生存更为艰难。据2007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数据;全国148家传染病院中有63.51%出现亏损,在所有传染病医院中,当年结余占总支出比例大于5%的仅12所,减除财政专项结余后,148家传染病医院亏损5.98亿元。
设有床位的综合医院感染科与传染病专科医院之间,还存在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关系。当综合医院感染科发展较好时,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经营就更为困难。2007年的数据还显示,传染病专科医院经济效益低于同级综合医院,其人员收入水平也低于综合医院。王贵强说,在传染科专科医院,为增加营收,还会出现本来无须住院的病人却被收治入院的情况。
缪晓辉说,在医疗服务被推向市场化后,感染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在医院各个科室中处于最低一个层次的水平。赵晖称,自己科室的护士2019年有好几个月奖金是每月3000多元,基本工资一两千元,与清洁工的收入相差无几。自己有几个月的奖金是每月6000元,相当于他的大学同学奖金收入的五分之一。杨友明工作31年,每一年收入的增长幅度仅维持在5%左右,有时候还会负增长。在美国,感染科医生的收入虽然只有心内科、外科医生的 1/3 到 1/4,但平均下来年薪能有15万美元,王贵强认为,中国感染科医生也要保证其一定的底薪,才能使得学科顺畅发展。
待遇偏低,感染科的发展受困,加上社会普遍对传染病的排斥等多个因素,使医学院毕业生普遍不愿意到感染科工作。杨友明所在的科室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进来新人,科室只有二十来个人的规模,一旦科室人员想要到外地进修学习,就会令日常运转难以维系。在华山医院,翁心华说,2000年前后,感染科也有一部人因为待遇低选择离开,如今的网红医生、现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博士毕业后也曾和翁心华说,想另谋出路。
作为中国感染学科发展的“重镇”,王贵强所在的北大第一医院感染科的床位数长年来一直没有增长,近期还因楼宇改造,被压缩到一半,仅有30张。感染科的人才队伍自2003年SARS后补充了两名新人之后,至少有12年没有再进人,“这从客观上影响了整个学科的梯队建设。”王贵强说。
“平战结合”与建设“大感染学科”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传染病专科医院在病患综合救治方面显得力量薄弱。据媒体报道,在武汉金银潭医院,ICU只有五位医生,全院的各类氧疗仪器加起来不过20台。一个月时间里,面对涌入的患者,医院四个普通病区被改造成ICU病房,武汉市多家医院及全国多地派出医疗队前去支援。在湖北省黄冈市,SARS后建立的黄冈市传染病医院因平时没有足够多的病人,多年后已变成一片废墟,这次疫情到来时,黄冈市对其进行了紧急改造,还提前启用了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王贵强认为,当下中国感染学科面临的现状是平时没有传染病大流行,感染科不受重视,传染病一来,又显得难以招架。他分析说,感染学科的发展要“平战结合”,感染科医生除了要会看肝炎、结核病,还要培养诊治各类非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能力。“不明原因发热是重要的一个抓手,可以锻炼感染科医生的基本功”,而肝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病率会进一步下降。同时,感染科医生要介入临床微生物病原诊断和院感防控。王贵强将这样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称为“大感染学科”建设。
张文宏所在的华山医院参与了上海市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基因组测序工作。他认为,感染科与临床微生物科要担负起对病原体的鉴定、对疾病早期识别的使命,守住第一道防线。翁心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感染性疾病来说,病原体的诊断尤为重要,一定要在有条件的三级医院建立实验室。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感染科医生也扮演着多重角色。王贵强说,平日里美国感染科医生要参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参加医院多学科的会诊,指导抗菌药物的使用,同时兼着院感工作。除本职外,感染科医生有的就是微生物专家,还有在公共卫生方面颇有建树者。重大疫情发生时,感染科医生能够站出来,参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决策。
将感染病诊治、微生物病原体检测、院感控制结合起来,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感染学科是美国模式的体现。王贵强说,将三个处于较为薄弱地位的学科和科室有机整合,能提高效率,提升感染科医生能力,也能增加科室收入。当重大疫情来临时,感染科还能和呼吸科、ICU等其他科室联动。在王贵强看来,这是在综合性医院壮大感染科的必要性所在及发展路径。
翁心华将传染病专科医院比作“消防队”,“消防队员不是每天要救火的,但是需要救火的时候,这批队伍马上可以拉出去用。”他认为,传染病专科医院如果平时只收治传染病,业务量太小,难以为继。他建议这类医院可以像综合医院一样,增加一些其他科室,来充实自己的力量。他举例说,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当地原来的传染病专科医院,有三百多张收治传染病人的床位。但在平时,医院开展外科手术、内科各类疾病诊治的业务,做到“平战结合”。这方面转型的范例还有北京地坛医院。2010年,地坛医院确立了“以传染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发展目标,先后建立了儿科、眼科、口腔科、心内科等科室。
王贵强分析说,目前,没有必要再大规模建立新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但重要的是,要将现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往综合医院方向转变,加强这些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而传染病专科医院的一大优势在于,拥有符合传染病收治条件的隔离病房。缪晓辉说,此次疫情过后,国家层面要加大投入,各级综合性医院都应设置一定数量的负压隔离病房,平时负压病房可以不启用。床位闲置时,可用来收治其他病人。
这次疫情中,湖北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且大部分是非感染科的医生。在美国,院感工作更倾向由有临床经验的感染科医师来负责,“这是一种专业化管理,需要很强的临床知识储备和实践。”王贵强分析说。而中国在SARS之前,院内感染部门的岗位多由护士担纲。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就透露说,他们医院院感部门就是由有院感知识的护士负责。SARS之后,一些医院院感科负责人由感染科主任兼任。
关于大感染科的建设,王贵强还有一个考虑,希望医疗机构内与感染相关的几个科室与疾控部门能有一个好的融合与互动机制,人员相互之间往来,最好是能像美国那样,医院的感染科医生同时是公共卫生专家,对政府的决策有建议建言的渠道与权利。2003年SARS过后,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提过这样的想法,并进行过讨论,王贵强也参加了,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这次疫情后,王贵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新考虑这一提议。
今天,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老传染病也出现新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多重耐药结核病的出现。感染医学在人类与微生物的较量中要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减轻,而是越来越重。抗生素与疫苗的胜利曾让一些人认为,我们再也不需要感染病专家了。“我想,今天没有人会再抱有这样的想法。”哈佛大学医学文化学教授大卫·琼斯说,不管是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部分,还是出于对免疫受损人群的照护,感染医学正在蓬勃发展。它的命运,只会随着2020年的新冠病毒暴发而愈发兴盛。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0期
 与歌迷合唱戴佩妮掐大腿忍笑 细数演唱会尴
与歌迷合唱戴佩妮掐大腿忍笑 细数演唱会尴 刘若英当导演自称像家长 陈奕迅唱主题曲到
刘若英当导演自称像家长 陈奕迅唱主题曲到 吴越《北京女子图鉴》变人生导师 成戚薇“
吴越《北京女子图鉴》变人生导师 成戚薇“ 法律专家谈抖音被黑:如属恶意诋毁则涉嫌刑
法律专家谈抖音被黑:如属恶意诋毁则涉嫌刑 重男轻女、亲情压榨……国产剧为何频现“奇
重男轻女、亲情压榨……国产剧为何频现“奇 电影《动物世界》曝光最新预告 李易峰开启
电影《动物世界》曝光最新预告 李易峰开启 公园游客增多游园莫忘防护 专家:拍照不扎
公园游客增多游园莫忘防护 专家:拍照不扎 二季度王牌综艺回归 新综艺靠创意吸睛
二季度王牌综艺回归 新综艺靠创意吸睛 李玉刚执导舞台剧 用现代艺术演绎传
李玉刚执导舞台剧 用现代艺术演绎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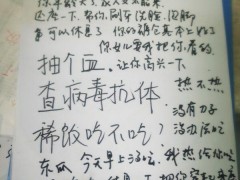 92岁武汉奶奶即将出院 留下21页护士
92岁武汉奶奶即将出院 留下21页护士 方舱"读书哥"今天回家了! 还拿到了签
方舱"读书哥"今天回家了! 还拿到了签 国家电网:下决心退出房地产业务
国家电网:下决心退出房地产业务 福建泉州:“云沙龙”引导青年创客“
福建泉州:“云沙龙”引导青年创客“ “女子图鉴”系列剧将播 编剧:没有
“女子图鉴”系列剧将播 编剧:没有 一线抗疫群英谱丨陈红:告别这个城市
一线抗疫群英谱丨陈红:告别这个城市 邓伦节目中推理三发三中 穿花围裙走
邓伦节目中推理三发三中 穿花围裙走 统筹抓好改革稳定工作:各行业积极恢
统筹抓好改革稳定工作:各行业积极恢 马东学beatbox惹爆笑 奥运冠军何冲分
马东学beatbox惹爆笑 奥运冠军何冲分 与迪丽热巴一起,闯荡《烈火如歌》燃
与迪丽热巴一起,闯荡《烈火如歌》燃 黄子韬巡回演唱会主海报曝光 视觉冲
黄子韬巡回演唱会主海报曝光 视觉冲 《以你为名的青春》校园风引回忆 连
《以你为名的青春》校园风引回忆 连 刘德华古天乐加盟《扫毒2》 6月启动
刘德华古天乐加盟《扫毒2》 6月启动